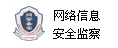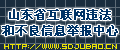唐高宗李治(公元628年-公元683年),继李世民为帝。李世民共14子,属长孙皇后所生者三子,长为承乾,次为泰,三为治。在李世民14个儿子之中,最有可能立为太子的,当是长孙氏所生三子;在长孙氏所生三子中,最先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子李承乾。遗憾的是,李承乾被立为王储15年,终因品行太坏而被废为庶人。这是李世民执政期间,皇室内部一次不大不小的权力纷争。
李承乾8岁时被李世民立为太子,史称李承乾“性聪敏”,很受李世民的宠爱,但是,李承乾稍长之后,品格日坏:
初,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畋猎,所为奢靡,畏上知之,对宫臣常论忠孝,或至于涕泣,退归宫中,则与群小相亵狎。宫臣有欲谏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辄迎拜,敛容危坐,引咎自责,言辞辩给,宫臣拜答不暇。宫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时论初皆称贤。(《资治通鉴》卷196)
这里讲的“退归宫中, 则与群小相亵狎”,是指李承乾建造大铜炉,“六隔大鼎 ”, 然后盗取民间牛马,亲自烹煮,与下属分割共食。又常常扮作突厥人的模样,装作可汗死状,让下属痛哭……公开宣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毫无帝王气象。更为严重的是,李承乾与亲弟弟李泰之间,有权力之争:
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承乾意泰告讦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象,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 (《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承乾酷好男风,因男宠而构恶于父亲和弟弟,其卑琐之状,令人可笑。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齐王李祐因不服李世民管教,公然反叛。李承乾乘机企图刺杀李世民。李承乾对刺客纥干承基说:“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企图配合齐王李祐,一起对付李世民。齐王败,纥干承基原与齐王瓜葛,被捕入狱,一并交待李承乾的阴谋,李承乾被废为庶人。生活作风的差异,政治修养的差异以及对权力的心态失衡,导致父子、兄弟之间的种种矛盾。李承乾和李泰的矛盾,使得李世民重新物色太子:
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 (《资治通鉴》卷197)
这就是说,立太子产生了不同意见。长孙无忌等人坚决主张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李世民和一部分大臣主张立魏王李泰。李世民转述李泰的意见,让他做皇帝,将来杀死儿子,将皇位转让给弟弟李治。这个意见遭到褚遂良的反对,他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这个反驳是有力量的,当李世民活着的时候,李承乾、李泰尚且争斗不休,待李世民死后,李泰有可能杀子让位吗?当然不能!褚遂良逼进一步,直接批评李世民,说:“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将李承乾与李泰争权位、争宠幸之罪,一古脑儿加在李世民身上。褚遂良的意见虽然委婉,但却严肃而认真,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事实上,李世民与承乾和李泰之间确乎有复杂而微妙的权力纷争。所以褚遂良一步不让,向李世民提出了严肃的警告:“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李世民当然不可能为了立李泰而处置李治,再说也没有任何理由处置李治。此时,李泰的不轨行为又被李世民发现,才后悔立李泰的主意。决心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 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谢。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 (同上)
这就是高宗李治被立为太子的经过,甚至也可以说是李承乾、李泰鹬蚌相争,李治是渔翁得利。另外,立李治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起了关键作用。这对李治封禅泰山以及携带武则天一起去泰山,都起了极微妙的心理作用。
关于立李治为太子,《新唐书》颇有非议,以为“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童昏。高宗溺爱袵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这当然是旧的正统观念看问题,以为武则天不该当皇帝,而武则天之所以能当皇帝,错在高宗李治身上,连类而及,太宗立李治为太子,自然也大错特错。其实,问题并不如此单纯。武则天当也并非十恶不赦,其实李世民的错误,在立李承乾时就发生了。贞观二年立李承乾为太子,时年仅8岁。虽然李世民派了得力心腹管教,但李承乾日益骄纵。后来,李世民以重视李泰来平衡抑制李承乾,事实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李承乾的骄纵不仅没有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李泰又萌发了夺太子之位的贪心。等到李承乾企图刺杀李世民的阴谋败露之日,李世民左右为难。所以褚遂良指责李世民,说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与李泰之间的关系上,行为不当,以成大祸。其实,李世民也确实知道李治“仁厚”。所谓“仁厚”是客气之词,实际上就是“无能”,因而在李承乾失败之后,他提议李泰。但是,长孙无忌等人坚决反对。李世民有错在先,李泰又有过失在后,长孙无忌是近亲、忠臣、影响大,在朝廷中颇有实力,他力主立李治,可以说李世民是被逼迫的。说李世民“昧于知子”,大概冤枉。立李治为太子时,李世民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治被立为太子,是长孙无忌的主张,而不是李世民的主张。但是,李治“愚”有“愚福”,上承父亲李世民的余绪,内有干练的武则天相助,虽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伤害了不少不该伤害的人,但从历史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尚无大过。过去的历史学家称他有“永徽之治”,虽不是他个人的作为,至少是承家风而不败,似不应毁之太过。
唐高宗李治封禅泰山,最大的特色是他带皇后武则天,并且允许武则天参与祭祀典礼活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地悠悠,一大创举。

武则天(公元624年-公元705年),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关于她进入宫帏,《资治通鉴》在贞观十一年条下说:“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将武则天选入后宫,完全是李世民的主意,李世民时年38岁。武则天入宫,李世民似乎特别兴奋:
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闻士彠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母杨,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母韪其意,止泣。既见帝,赐号武媚。
武媚在宫中为才人,与李世民相处13年。史书、笔记未见有记载。大概在宫中无出格之举动。李世民逝世,她被李治注目,引入宫中:
及帝崩,与嫔御皆为比丘尼。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王皇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它日,帝过佛庐,才人见且泣,帝感动。后廉知状,引内后宫,以挠妃宠。 (《新唐书.武则天传》)
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即皇帝位后,就大赦天下和出宫人。所谓出宫人,就是将老皇帝搜罗到后宫的宫女放出宫廷。李世民即帝位时,一次就放出3000人。《新唐书?武则天本纪》说“太宗崩,后削发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 ”,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武则天再与李治结缡,主要责任似乎也不在她身上。高宗身为太子时,就对武则天垂涎。高宗皇后请武则天入宫,一方面讨高宗李治欢心,一方面用武则天来抵消萧淑妃的宠幸,遏制萧淑妃的势力。当然,武则天也利用高宗李治、王皇后和萧淑妃,利用他们的矛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我们不能只承认王皇后、萧淑妃有利用武则天的资格,而不承认武则天有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资格。在政治游戏中,谁的手段高明,谁就是胜利者。《新唐书》作者的历史观念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将武则天列入《本纪》,以帝王的资格对待武则天,一方面又将武则天视为“女祸”,视同周幽王之褒姒: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周幽王之诗也。是时,幽王虽亡,而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而诗人乃言灭之者,以为文、武之业于是荡尽,东周虽在,不能复兴矣。其曰灭者,甚疾之之辞也。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
且不说西周的结束是不是真的因为褒姒,也不说“女祸”说在中国政治史中的历史价值如何,单就武则天而言,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将她与褒姒画等号。诚然,武则天确实做过许多不该做的事,也确实伤害过许多不该伤害的人: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无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这就是骆宾王著名的痛诋武则天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除了情绪性的词语而外,就叙事而言,大都是有依据的,只有“弑君”一词,未知何指。我们不想重复骆宾王所指陈事件,只想指出,上述事件,有时也是不得已的。父子同爱,是父子的事,不能全推给武则天,因为此“父”此“子”均非常人,都是一代帝王,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抗拒是相当困难的,与其抗拒,不如利用。所以武则天就充分利用了李世民父子的弱点,为自己谋求帝王之尊作铺垫。政治家看重的是目的。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使用一些权术,势所难免。历史学家的着眼点应该是社会生产力。如果政治游戏的规则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破坏,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失败的,反之,就是成功的。抽象地评述政治家的某些个人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充其量是孩提之见。说起来,完全正确,但对历史却毫无意义。武则天无论是在辅助高宗李治的年代里,还是好垂帘听政乃至干脆做皇帝的年代里,并未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并且维持了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良好政治经济局面。
武则天亲近高宗李治之后,由昭仪而皇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又进号“天后”。此时,武则天提出12条建议: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这12条,是高宗李治在位,她实际掌权的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提出的,从标目看,这12条是有利于当时的朝廷政治稳定,特别是“ 劝农桑薄赋徭”、“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省功费力役”数项,对发展社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较为重要的措施。“广言路”、“杜谗口”诸项,对政治稳定有益。当然,任何一位统治者,他(她)的“广言路”和“杜谗口”都有政治性利益、自身利益、社会利益三个方面,只是由于统治者本人的素质不同,价值取向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昏庸的统治者就是依据自身利益的价值标准,来“广言路”、“杜谗口”,其结果,奸言、媚言、诬言横流;忠良之言、谏诤之言、批评之言销声匿迹,于是,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自取灭亡。当然,也有的统治者在三者之间作不同程度的调节,出现不同侧面的价值取向,取得不同程度的社会效果。其中最佳的应当是以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标准,不断地遏止自身利益的欲望,出现上历史所谓“太平盛世”。屈指算来,唐太宗李世民堪当其任。至于武则天,我觉得她能够在三者之间进行依违调节,比较巧妙地运用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杠杆,最终达到自我利益的目标,虽不无权诈之嫌,亦不无狠毒之态,但毕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将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是应当肯定的。武则天的12条建议,是体现了这个政治运行规则的。
后来,高宗李治逝世,武则天由垂帘听政而登上皇帝宝座,公开地做皇帝。不过,武则天是很聪明的,她深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特殊性,女人要做皇帝,比男人有加倍的困难。因此,就必须有非常的措施,有非凡的手段。我想最有特色的是两条,一是延揽人才,二是听取意见。 请看《 新唐书.后妃传》的记载:
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又畏天下有谋反逆者,诏许上变,在所给轻传,供五品食,送京师,即日召见,厚饵爵赏歆动之。凡言变,吏不得何诘,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变者徧天下,人人屏息,无敢议。
这一段文字,表述了武则天两件事,一是搜罗人才,二是查寻反对派。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只不过一反一正而已。中国古代封建意识形态的特色之一是重男轻女,而且根深蒂固。一个女人企图在政治格局中发挥作用,十分艰难,若想做皇帝,就是“难于上青天”。武则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登上皇帝宝座。武则天面对的是李唐王朝的后裔及其强大的有深刻影响的臣僚体系。因此,武则天要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就必须有非凡的措施。这其一便是搜罗人才。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政治格局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则,说不可以一朝天子一朝臣,不过是句客气话,说给他人听的,造造舆论而已,真正运作起来,还必须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如此,不是政权不能巩固,便是运作不灵,障碍重重,矛盾重重。武则天深谙此理,为巩固权位,就着意搜罗人才,或者说培植党羽。《新唐书》作者,虽然意在贬抑,但符合事实,说“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言有所合”是武则天的取人标准,“至不称职”,则必诛废,决不因“言有所合”而苟容,所以就一定能选拔到“实才真贤”。有了“实才真贤”,就可以和李唐王朝的不合作大臣相抗衡。收拾山河需要人,而这人,必须是有真才实学而又观念相似的人。其次,天下之大,人员之众,要加强统治,就应该信息灵通。在特殊的情势下,信息灵通,将各种反对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所谓防微杜渐,可以减少重大政治反叛发生的概率,因此,武则天的第二大措施就是“诏许上变”。“上变”就是允许各地向皇帝告发变乱事象。“上变者遍天下”,使得政治上的反对派侧目而视,不敢轻举妄动,确乎起到了震慑作用。遗憾的是,她心态失衡,也杀了不少不该杀的人,但是,一遇到此类事态发生,她又毫不留情地杀掉告发者和行刑者,以平民愤。表面上看,是玩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术,但实质上,却是武则天巩固帝位所不可缺少的。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政治派别的成败是非,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与发展。因此,武则天以“上变”来加强统治,巩固政权,无可厚非。
武则天即帝位之后,另一项措施是“铜匦”:
乃冶铜匦为一室,署东曰“延恩”,受干赏自言;南曰“招谏”,受时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 通玄 ”,受谶步秘策。所谓“铜匦”,就是意见箱。接受意见,分门别类。如果人们反映的意见都能被重视,在封建社会亦是幸事,总比求告无门,无处申冤的好。其次,“铜匦”制在沟通朝廷上下之间的意见,听取民情民意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有防止“塞壅蔽” 的意见, 他们以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是政治清平的标志。尽管武则天设“铜匦”,也有消灭异已的的意味,但毕竟也有了解下情的作用。凡此等等,都使武则天的权力日趋巩固,反对派不是被消灭,就是被遏止了:
始,武承嗣请太后立七庙,中书令裴炎沮止,及敬业之兴,下炎狱,杀之,并杀左威卫大将程务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群臣廷让曰:“朕于天下无负,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 太后曰:“朕辅先帝踰三十年,忧劳天下。爵位富贵,朕所与也;天下安佚,朕所养也。先帝弃群臣,以社稷为讬,朕不敢爱身,而知爱人。今为戎首者皆将相,何见负之遽?且受遣老臣伉扈难制有若裴炎乎?世将种能合亡命若徐敬业乎?宿将善战若程务挺乎?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蚤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诒天下笑。”群臣顿首,不敢仰视,曰:“惟陛下命。” (《新唐书.后妃传》)
这件事发生在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失败之后。武则天对臣僚的训话,是极富于挑战性的,而“群臣顿首,不敢仰视”,也是真实的。综观武则天一生,无论是辅助高宗执政时期,还是在高宗身死之后自行执政时期,武则天都堪称御人有术,能维持政治格局的稳定与运行。因此,我们可以说,武则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最成功的女政治家。
据《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记载,麟德元年(公元664年)7月,“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其实,唐高宗李治做皇帝,事情总是由武则天办理。这是因为李治多病而又无能,武则天精明强干而又野心勃勃。所以说,如果以为高宗李治下诏封禅泰山,不如说是武则天要到泰山去封禅祭天。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影响下,武则天要到泰山,参与封禅大典,应该是一个艰苦的历程。《旧唐书》卷23《礼仪志》说“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是可信的。显而易见,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武则天要实现上泰山封禅的愿望,就首先要借高宗李治这杆旗帜。“密赞”是武则天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当高宗李治决定封禅泰山之后,武则天又提出了第二项措施,要参加泰山封禅仪典过程,实现武则天本人封禅泰山的目的:
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光。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哉?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期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省俗,意在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已。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妾谬处椒闱,叨居兰掖,但以职惟中馈,道属于?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苹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祇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今属崇禋,届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睠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梁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忱,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 (《全唐文.请亲祭地祇表》)
武则天的这则短文,对唐高宗李治是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有极强的说服力。众所周知,李治被李世民立为太子,实在是依靠了“ 母党 ”的政治势力,舅舅长孙无忌是坚决主张立李治为太子的人。李治即帝位之初,也全赖长孙无忌的辅助。武则天以为,祭祀天地、祖宗,自然要祭祀父母。而“推尊先后,亲飨琼筵”,怎么可以用一般男性大臣来进行典礼?这个做法实在是违背世故人情与典章制度的,既然一般的男性大臣不应该参与祭祀女性祖先的活动,那么,祭祀李治母亲长孙皇后的典礼,就只有处于“ 椒闱 ”的现世皇后武则天来主持,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更有甚者,武则天还自称“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讲求孝道,子女辈于父母辈,要早晚请安,时称“晨昏定省”。所谓“早乖”,是和武则天的生活经历有关,也和高宗李治个人行为有关。就身分而言,武则天14岁入宫廷,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和长孙皇后虽有主子、奴才之分,但却不是婆媳关系,无需乎“晨昏定省”。太宗李世民逝世,武则天通过削发为尼改变形象,和高宗李治结合,终于成为李治的皇后。此时此际,倒应该认真地尽孝道,进行“晨昏定省”。然而,长孙皇后早已逝世,所以说“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唯一补救的办法,趁高宗封禅泰山,祭祀天地、祖宗、父母的时机,与高宗一起赴泰山,“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以尽孝道,以叙婆媳关系,以正名分。而这,高宗李治是不可以不认可的。由此可见武则天之精明能干,智慧超群。
那么,武则天是不是真心诚意、心一意地去祭长孙皇后并确认婆媳妇关系呢?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是“显号”、“觊名”,为走向皇帝宝座铺设红地毯。武则天深知,唐太宗李世民才人、感业寺比丘尼、高宗李治的昭仪、皇后的经历,虽然节节登阶,但每一个台阶都耗费了翻江倒海的力气。要以女人的身分登上执政宝座的最高层,是十分艰难的,前人的教训,自身的体验,都使她明白,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必须抓住每一个应该抓住的机会,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必须玩弄一切可以玩弄的心计,不懈地努力,才能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目的。武则天不仅在朝廷大臣间利用矛盾,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利用佛教、道教,乃至泰山封禅。按照有关部门的建议,“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由于武则天的上述短文,“于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大妃为终献”,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史上一项创举,女人第一次在封禅泰山的盛典中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地位。最为有趣的是,细读武则天的《请亲祭地祇表》,她在道德伦理上承认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政治伦理,承认等级制,承认男女有别的文化心态,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不平等的男女观念来达到平等的男女地位,为自身走向与皇帝平等的地位铺平了道路,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高宗李治的封禅泰山,经过认真的准备,随从封禅的队伍十分庞大,李治曾命令各地的重要地方官员,聚集泰山,参加盛典:
宜以三年(按,指麟德三年,实际上是乾封元年,下此诏时,尚未改元)正月,式遵故实,有事于岱宗。所司详求茂典,以从折衷。其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诸王十月集东都。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天下诸州,明扬才彦,或销声幽薮,或藏
器下僚,并随岳牧举送。 (《举行封禅所司集岳下诏》)
高宗李治的诏书,文如其人,无才华之语,有谨慎之心,无权威之势,有实在之诚。都督刺史集岳下,为封禅大典之盛;边远州郡安居不动,以防不测;诸王定要集中洛阳,随驾东行,既显亲情,亦显尊贵。高宗李治和历代帝王封禅泰山一样,事前都要作一些准备,特别是礼仪制度上的研讨。高宗时的礼官、博士所陈述的礼仪制度无非是祭坛的规模大小,形式的方圆,石料的品种而已,虽然变化多端,但大体不出旧有的规格。只是这一次封禅仪注,对斋戒有较详的记叙:
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斋戒。于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于行从中台,云:“来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禅社首。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上斋于行宫四日,致斋三日。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事群官、诸方客使,各本司公馆清斋一宿。前祀一日,诸卫令其属:未后一刻,设黄麾半仗于外之外,与乐工人俱清斋一宿。
中国古代,“斋”和“斋戒”的内容大体一致,一般说来,“斋”、“斋戒”是指祭祀、典祀之前的清心洁身,例如沐浴更衣,不吃荤菜,不饮酒,清心寡欲,戒除妄念,以示虔诚。具体细节,各种宗教,不同祭祀仪式,不同的典礼要求并不相同,但是,身心清洁,诚心诚意,却是一致的。从上述文字看,李治封禅泰山,所有参与的官员、侍从、使节,都必须进行斋戒,可见其虔诚程度。
麟德二年,10月,李治从洛阳出发,赴泰山进行封禅:
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资治通鉴》卷201)
这段文字,提供了许多背景材料:李治封禅,连年丰收,斗米值五钱,天下丰裕。在封闭性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粮价低贱,说明粮食充足,粮食充足,就天下太平。因此,李治封禅,就经济而言,是天下富足而安定。“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的朝会使者,各帅领下属随李治封禅泰山。高丽,今朝鲜;波斯,今伊朗;乌长,亦作乌苌,今印度。在如此广大的范围,或属于唐王朝的少数民族,或属于归顺唐王朝的独立国家,或属于与唐王交往密切的友好国家,一言以蔽之,这个事实说明当时唐王朝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十分强大,在周边国家中有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据史书记载,高宗李治在到泰山的路程中,十分愉快。当他到达“濮阳”(今河南县名)时,问窦德玄:“濮阳人称‘帝丘’,为什么?”窦德玄不知究竟,无言可对。许敬守回答说:“古时颛顼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帝丘。”李治听了十分高兴。许敬宗走了之后,李治说:“当大臣不可以没有学问;我看窦德玄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内心里替他羞愧。”窦德玄听了这话不服气,进行反驳,说:“人有能话不能,我不知道不勉强回答,这正是我的优点。”李勣做总结:说许敬宗知道得多,很好;窦德玄的话也十分有理。这一则故事,说明李治和大臣在路上心情轻松,十分愉快。李治在路上办的另一件事是给寿张张公艺祝贺: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冲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寿张是山东县名。张公艺“九世同居”,靠的是一个“忍”字。张公艺说的也许是实话,但九世同居,靠“忍”字维持,确乎艰难不易。众所周知,维系家庭关系,人们可能有许多办法,但说到底,家庭的命根子是经济。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家庭就可以维持,丧失共同的经济利益,家庭就解体,父子、夫妻概莫能免。道德伦理、文化心态……只是一贴贴酸甜苦辣的调味剂。张公艺抛开其他因素,突出一个“忍”字,十分新鲜,李治对乃父与叔伯父之间的关系、自身与兄长李承乾、李泰之间的关系深为了解,深感能“九世同居”之不易,所以感慨良多,大加称道,并“赐以缣帛”。
《旧唐书》卷23记载唐高宗李治封禅泰山,用取水火之器取火于日,取水于,甚为新鲜。秦汉封禅,未见此举。兹抄录如下:
丙辰,前罗文府果毅李敬贞论封禅须明水实樽:“《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云:‘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数石。’王充《论衡》云:‘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水于月,相去甚远,而火至水来者,气感之验也。’《汉旧仪》云:‘八月饮酎,车驾夕牲,以鉴诸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云:‘鉴燧,取水火之器也。’准郑此注,则水火之器,皆以金锡为之。今司宰有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阴鉴形如方镜,以取明水。但比年祭祀,皆用阳燧取火,应时得;以阴鉴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替明水之处。”奉敕令礼司研究。敬贞因说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礼》金锡相半,自是造阳燧法,郑玄错解,以为阴鉴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诸,引《淮南子》等书,用大蛤也。”又称:“敬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奉常奏曰:“封禅祭祀,即须明水实樽。敬贞所陈,检有故实。”又称:“先经试验确执,望请差敬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与所司对试。”这一段文字叙述冗长,其实很简单。封禅泰山,举行祭祀,需用水火。但水火不是人间通常水火,必须是明水明火。所谓明水明火,即今日之天水、天火。取天火之法是阳燧,即以金锡各半制成圆镜形器具,聚焦成火。实际上可能类似今天的太阳灶。所以说“取火于日”。这个圆镜形器具,人称“阳燧”。同理,古人称有阴燧,亦用同样的材料方形镜器具,但试验不得水。于是考查古书,郑玄注释错误,应该改从《淮南子》的说法,不用金锡各半制成的阴燧,而用大蛤。试验结果,果然得水。于是,向高宗李治建议,不用郑玄说的“阴燧”,改用《淮南子》上说的“方诸”。“方诸”,就是大蛤。郑玄是东汉的大儒,他的《五经注》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性的解释,要改变,要纠正,自然要费很大的周折。对于这件事,高宗李治下了一道很开明的诏书:
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独不改张,斯乃自处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禅,即用玉牒金绳,器物之间,复有瓦?秸席,一时行礼,文质顿乖,驳而不伦,深为未惬。其封祀、降禅所设上帝、后土位,先设稿秸。瓦?、瓢杯等物,并宜改用裀襑罍,每事从文。其诸郊祀,亦宜准此。
从字面上看,这个诏书并不是针对前边说的明水明火问题,也不是针对阳燧和方诸问题,而是针对封禅典礼的仪式,但是,《旧唐书》的作者在《礼仪志》中确实将它放在明水问题之后,并且以“是日”相连接。因此,我们以为封禅之前高宗李治研究的问题甚多,诏书从简,只涉及瓦?秸席之类,其精神实质是不必一切从古,今人不用“瓦?”, 而用“罍爵”, 所以改用“罍爵”。不言而喻,阴燧或阴鉴不能取明水,用方诸才能取明水,那就不用阴燧或阴鉴,就改用“方诸”,本属正常。但是,秦汉之际,儒生往往食古不化,不敢按实际情况便宜行事,一味信古崇古,甚至引经据典,议论纷繁,难衷一是。所以,秦皇、汉武皆不用儒生之论。唐太宗李世民虽然用儒生研究问题,但决定问题,只由少数人拍板。李治更是提出“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 的观念。 并且进一步指出,不随代改革是不对的,是“自处于厚,奉天以薄”,是不尊敬天地神祗的行为。所以,高宗李治虽然仁厚少能,却能因时适势,不固执偏见,却也是个优点。
高宗李治封禅泰山的事件过程,《资治通鉴》描述清楚而简洁,麟德二年十二月,“车驾至齐州,留10日。丙辰,发灵岩顿,至泰山下,有司于山南为圆坛,山上为登封坛,社首山为降禅方坛。”至此,似乎万事俱备,只待举行正式的封禅祭天祀地大典:
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已已,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玉玺,藏以石?。庚午,降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皇后升坛亚献,帷帟皆以锦绣为之;酌酒,实俎豆,登歌,皆用宫人。壬申,上御朝觐坛,受朝贺;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这里讲了三件事。一是封禅泰山典礼的全过程。二是皇后武则天参加降禅社首的仪式,程序列为“亚献”。采取的措施是以宦者执锦绣帷帟以阻隔内外,皇后在帷帟之内,大臣随从在帷帟之外。《新唐书.礼乐志》说,当武则天在帷峦之内举行祭祀亚献时,“群臣瞻望,多窃笑之。”三是随从封禅泰山的官员,皆加官晋爵。
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封禅,与秦皇汉武相比, 虽然在个人功业上难以抗衡,但在思想境界和文化心态上却大大前进了一步。秦皇汉武的封禅泰山,除了政治因素而外,勿庸讳言,他们个人心灵深处都有迷信神仙,祈求长生不老的因素,而李治和武则天,除了政治企图相同而外,在个人心态上虽不无迷信的成分,主要还是利用封禅追求个人的政治目的,在李治,是通过封禅“告成功于天”来“显号”、“觊名”;在武则天,则是通过封禅祭天,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为走向皇帝宝座作舆论准备。这和她利用佛教《大云经》的做法是一致的,当有人发现《大云经》中有女性佛时,她兴奋备至。女性的地位提高,武则天的地位也提高;女性可以成佛,武则天当然可以做皇帝。只是武则天的愿望无法写在封禅祭祀的《玉牒文》里,不过高宗李治的愿望却明明白白写在《玉牒文》里。秦皇汉武求长生不死,是个人秘请,所以《玉牒文》不便公开,只好隐秘。高宗李治的“显号”、“觊名”,是通过宣扬祖宗的功德和个人政绩来进行,正大光明,所以就敢于公开。公开《玉牒文》是高宗李治封禅泰山的一大特色,值得一记:
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极颠危,天数穷否,生灵涂炭,鼎祚沦亡。高祖仗黄铖而救黎元,锡元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谏石,定区宇于再麾,业比断敖,饮沧溟而一息。臣忝奉馀绪,承威积庆,遂得?山请燎,炎海韬波,虽业茂宗祧,实降灵穹昊。今谨告成东岳,归功上元。大宝克隆,鸿基永固。凝薰万代,陶化八纮。 (《全唐文.泰山玉牒文》)
所谓《玉牒文》是专指封禅祭天刻在玉石片上的祈祷性的文字。这种文章一要简短,二要明确,三要句式整齐。高宗李治的《泰山玉牒文》主要称颂高祖李渊灭隋建唐有功,太宗李世民治世有绩。至于他本人,叙述倒也客观,“忝奉馀绪,承威积庆”。李治确乎能承先人之馀绪,不是败家之子。高宗李治的愿望是四句话:“大宝克隆,鸿基永固;凝薰万姓,陶化八。”前两句说李唐王朝的皇运兴隆,江山永固,社稷永保。后两句说李唐王朝的恩泽遍布天下,施及万姓。就一般性而言,高宗李治的这个愿望比起秦皇汉武的个人秘请来,似乎光明磊落得多。这种玉牒文字刻在玉石片上,将玉石片叠放在一起,然后用金绳或银绳将玉石捆绑起来,封以金泥,加盖皇帝玉玺,埋在泰山。遗憾的是,泰山至今未曾发现这种地下文物。
李治封禅泰山, 将封祀坛命名为“舞鹤台”,将登封坛命名为“万岁台”,将降禅坛命名为“景云台”,以纪祥瑞。今天保存下来的文物有“双束碑”一通。双石条并套,同额同座,人称“鸳鸯”。碑上有武则天创制的文字:天,印刷体作“天”,碑作“?”。地,印刷体作“地”,碑作“埊”。日,印刷体作“日”,碑作“?”。月,印刷体作“月”,碑作“?” 等等。近人查证,是碑作于显庆六年(公元661年)。 据《旧唐书?高宗本纪》,正是显庆六年,武则天由昭仪晋升为皇后:
冬十月已酉,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大赦天下。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判定,双束碑上题记的最早时限是显庆六年2月。碑文是:
显庆六年二月廿二日,敕使东岳先生郭兴真,弟子陈兰茂、杜知古、马知止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 (《泰山历代石刻选注》)
准此,双束碑初制于显庆六年二月,时高宗李治的皇后是王氏,武则天是显庆六年十月才由昭仪晋升为皇后,不当提前8个月搞这个碑。但是,历代传说,双束碑为武则天制造。可能是看到碑上有武则天时的题记,又有武则天改制的文字,未加深究的缘故。其实,双束碑上的题记,其时限从显庆六年二月,到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甚至宋代尚有题刻。不过,最有意义的是最早的题刻。因此,双束碑是王皇后精心构想以固宠?还是昭仪武则天别出心裁以邀宠?还是道士们的异想天开以媚上?不得而知。但双束碑的形制确乎独具一格,启人幽思,令人遐想。
(责任编辑:张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