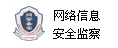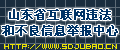|
据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我国7.51亿网民中,60岁及以上的比例达到4.8%。假设PC端和手机的使用偏好在各年龄段均匀分布,那么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手机网民规模约为3470万。老年人手机网民总规模庞大,增速也呈现加快趋势。另有调查显示,老年人一旦“触网”,手机及时通信的使用黏性甚至高于年轻人。 为什么是微信? 在诸多手机即时通信应用中,微信以绝对优势成为老年人最爱。这是微信产品特征和老年人行为特征奇妙组合的结果。在即时通信、社交互动这些核心功能层面,微信相比QQ等并没有本质区别,一统江湖的关键在于微信更加简单好用。 但微信的成功并不仅靠好上手。“语音通话+微信群+‘朋友圈’”的“三板斧”,让点对点、小群组、好友圈子紧密衔接,个人和社群信息向“朋友圈”的迁移极为方便。信息流动通路大巧若拙的设计,是微信生态枝繁叶茂的强有力保证。 相比工作生活都离不开微信的年轻人,老人的微信使用场景单一许多。与亲朋好友的日常联系、获取资讯,占据微信使用主要时长。这其中,三个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老年人会热衷微信。 其一,老年人社交圈子相对较小且固定,血缘、地缘、趣缘是“朋友圈”三大纽带,微信的相对封闭性、手机号码绑定注册等,都适合老年人的生活特征; 其二,家庭沟通在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中占据突出地位,微信在即时通信上的产品优势获得青年人认可并向老年人群渗透; 第三,老年人接触移动互联网的时间普遍不长,但社交媒体的“依赖症”仍然在发挥作用,这种“网瘾”不光表现在耗费较多闲暇时间上网,还表现在部分老年人在社交媒体应用上,由尝鲜感引发的攀比心理。 为什么是老人?
从2015年开始,“中老年人的‘朋友圈’”就成为热点话题,时不时被青年人拿出来吐槽一番。近两年,这一议题甚至发展到“拯救长辈‘朋友圈’”的程度。这样的呼声源于老年人“朋友圈”的一些普遍特征:“朋友圈”和社群的分享充斥生活类虚假信息,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泛滥,频打低俗、暴力、政治传言擦边球……另外,长辈“为孩子好”的习惯,在微信上变成了转发、催读。 上述问题,本质上是微信平台内容生态的特征,但唯独老年人“朋友圈”演变成为一种舆论标签,有一些值得我们讨论的原因。 观察传播现象,最直接的切入口是传播心理和传播动机。应当承认,大多数老年人转发和分享养生保健等方面信息的初衷是积极的,老年人抵抗力弱,对疾病疼痛有切身感受,对相关信息敏感性较高,养成了固定的阅读偏好。其向子女朋友的转发行为,大部分也是出于善意提醒与帮助。这种偏好和善意,往往在老年人的信息接收和转发过程中产生“宁可信其有”的传播心理。 “宁可信其有”,是传播中的博弈。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提出过被称为“帕斯卡赌注”的理论,核心可以类比为“宁可信其有”,即人们在未来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果对于任意可能的未来情况,现在选择A比选择B都能得到更好的效果,那么A就是最优解。在老年人微信信息传播过程中,“帕斯卡赌注”的博弈排列就是信、不信、不确定,转与不转(在这个决策过程中,[-2~2]分别代表决策收益:“2:众乐乐”“1:独乐乐”“0:什么也没有发生”“-1:挖坑埋了自己”“-2:给坑惨了,老铁”):
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信”和“不信”上,决策没有什么压力,毕竟选择-2对决策者没有什么积极收益(造谣者除外)。问题出在“不确定”的时候,如果选择不转,该信息的流动到此为止,决策收益为0;如果选择转,因为决策者对信息可信度没有把握,决策收益的预期在[-2~2]之间随机分布,总体决策收益趋向于0。 但这两者的决策收益相等只是表面上的,选择转载有更多可能性,特别是在当前聚合资讯类、即时通讯类手机应用虚假信息泛滥的内容生态之下,选择转载通常意味着虚假信息的扩散。这与很多老年人的积极预期正好相反。因此,作为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一种常见心理,“宁可信其有”在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上其实是不成立的,信其有并不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部分老年人在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上面对不确定性时,存在一种“转了让别人去分辨”的心理,当类似想法的人增多,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相应增大。 “长辈的‘朋友圈’”指向的问题,是老年人在面对事实上的虚假信息时,相对更多地选择“信”且“转”,“不确定”并“转”。舆论的忧虑,在于老年人整体上对信息辨识能力的降低。这个过程有两个路径: 一是老年人平均辨识能力不变下,“不确定”的老年人增多,这主要来自于老年人总量的增加。老年人因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社会阅历等在辨识能力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当下很多老年人对媒体的概念局限于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等于政府权威的观念较普遍,互联网媒介素养不足,把微信等同于报纸电视,将微信群和“朋友圈”文章当作权威。 二是老年人群体总量不变下,“不确定”的老年人增多,这主要来自于随着时间推移,老年人平均辨识能力的下降。老年人关注保健养生,是年龄和身体状况的自然影响,关注政治社会内容等可能有职业习惯的遗留。对这些方面虚假消息辨识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老年人脱离工作岗位后,社会活动范围缩小,网上网下“朋友圈”较为固定,信息来源减少且趋向单一,信息的更新迭代和交叉验证减少。封闭单一的生活状态,容易形成“信息壁垒”,影响对信息的判断力。 事实上,不管是老年人的平均辨识能力,还是老年人群体规模都是在变化的,在两个因子都在变化的情况下,老年人因生活状态变化导致的信息辨识能力降低,应当说是导致其社交媒体传播心态变化的主要因素。 要改善前述老年人“朋友圈”的问题,需要长辈们的觉醒、子女的义务、平台的自律和监管的责任。对老年人来说,提高虚假信息辨识能力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接触多元信息渠道,有意识地交叉验证,提高自身互联网信息素养。同时,也有必要自我约束“彰显消息灵通”“教育别人”等心理冲动。 对子女而言,吐槽并不能带来什么,放任自流也于事无补,即便难以用线下交流把长辈从“朋友圈”“抢回来”,也有义务指导长辈识别虚假信息。社交媒体平台和监管部门,有责任通过建立账号信用体系、虚假信息提示、针对老年人的信息保护等举措压缩虚假信息传播空间,净化平台环境。 (作者: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 贾伟民) (责任编辑:张鹏)
|

|